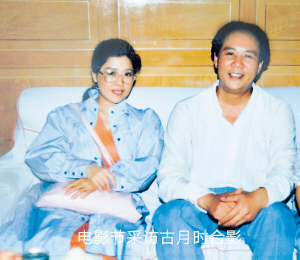 在电影节采访古月。
在电影节采访古月。 □ 张微微
缘起:白衣与墨香
1982年初夏,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证书尚未下发,命运的转折已悄然降临。5年临床医学的淬炼,终究不敌少年时埋下的文学星火。大学四年级时,学校艺术节征文活动上,我创作的小说斩获一等奖,刊登在校报头版,占据半幅版面。而另半版一等奖获得者,是高我十几期的校友、学长,时任卫生部《医院管理》杂志社副社长。因这一机缘,毕业前学长来校遴选编辑记者,点名录用了我。当同窗仍犹豫就业去向时,我已怀揣报到证,踏入设在省卫生厅内的期刊杂志社。
医学期刊的工作严谨而刻板,但我的笔从未停下。在整理医学文献的间隙,我仍会写诗、写小说,仿佛体内流淌着两种血液——一种属于手术刀与解剖图,另一种属于墨水与稿纸。
诗驿:太阳岛上的诵读
还是当医学生时,《哈尔滨日报》举办的“太阳岛诗会”,就在我眼前开启了另一扇窗。当端午的艾草香漫过松花江,我的诗作也在“太阳岛诗会”的诵读声中绽放。
连续几年,我的诗作都中选,除了在诗会上朗诵,还刊登在了《哈尔滨日报》太阳岛副刊上。因此,毕业工作后,我与副刊编辑部的各位老师们也更熟络起来。当年的副刊部主任李激扬老师,副主任柴烈老师,还有聂振邦、赵德海、李维基、富振忠、李铁、陶孟陶、王同君诸位老师,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他们更让我明白,文字的力量可以穿透时代的喧嚣,抵达人心的最深处。
破茧:三天的坚持
一天,我突然接到柴烈老师打来的电话,说《哈尔滨日报》改版,小报改大报,急招编辑记者,问我愿不愿意调过去?并说,这是副刊全体同仁一致的提议。我当然愿意了!
然而,难题接踵而至:原单位不放我走。我那时也来了犟劲,一心要去哈尔滨日报副刊部做我的“文学梦”,便一连三天去磨当时的杂志社社长。他去开会,我在门外等;他去食堂,我端着碗跟上;甚至他去游泳,我也跟着下水,在他耳边呱噪。三天后,社长终于叹了口气:“你这丫头,比病人缠着大夫还难缠。”最终,一纸调令为我铺平了道路。
当年和我一批调入哈尔滨日报副刊部的,还有李兰颂、李育民两位。那些为文学梦辗转的昼夜,最终都化作了副刊窗台上的第一缕晨光。
尾声:永远的哈报
如今回望,将我与哈报联系起的那根红线,原是无数双手共同编织起来的——是李激扬老师的慧眼识珠,是柴烈老师的提携引荐,是聂振邦等前辈的悉心指导,更是《哈尔滨日报》那永不褪色的红色报头,在我心头的萦绕。
在哈尔滨日报社工作近三十年的时间里,我在副刊部工作的时间最长,整整十年。先后做过科普、诗歌、杂文编辑,同时兼当文化记者。我连续十年参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报道,冲锋在哈市各项文化盛事报道的一线。当年全国红学会在哈市召开,我受领导委派去采访红学家蓝翎、李希凡,以题为《探索在一条红线上》的人物专访,受到社领导表彰。我随省作协组织的新闻采风团赴大庆油田采访,写出的报告文学《历史的脚步》,获全国第二届《“中国潮”报告文学征文》二等奖。此后,我分别当过医疗卫生、公检法、教育战线记者,可以说在新闻各条战线都历练过。在哈报工作的岁月,不仅仅历练了我的笔锋,更完成了我从医学生到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嬗变。
从医学院校毕业生,到哈尔滨日报记者,看似偶然,却不过是必然的另一种注解。正如诗行里的平仄,人生亦有着不可违逆的韵律。而《哈尔滨日报》正是我生命中那首最壮丽的诗。
作者 | 高级记者。1985年调入哈尔滨日报社。已退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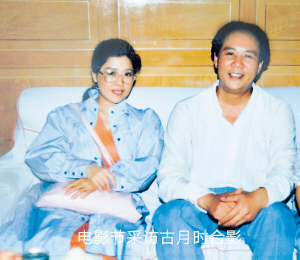 在电影节采访古月。
在电影节采访古月。 
